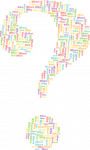忆理发
在我的记忆中,阴历二、五、八,我们所住的街道逢集。逢集日,天刚亮,剃匠们就担着剃头担子从不同的方向向街道南口走来,一付,两付,十多付。这便是剃头市。

一日收市,我在玩耍时看见一个剃头匠,肩上担着的竹板扁担,一头挑的是一个有抽屉的木箱,另一头是一个木架子,上面放着一个的铜盆。他走起路来一闪一闪地,扁担压弯到极限又弹起来,还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五十多岁的人这时间活象个二十岁的演员在舞台上表演。我在他身后学着他的走路,很好玩。“剃头来”,剃头匠喊得响亮,三个字儿拉得老长。妈妈听到了,把手从面盆中拨出,捋去大面疙瘩,扭着裹折了的尖尖脚,小跑走到大门口,“剃头的,剃一个头多钱?”“官行情,五分。”“好,给我娃剃个头。”我听到了,正要转身跑掉,没想到妈妈眼尖手快,用面手揑住了我的左耳,“看你的头发长成了小狗熊,再不听话我把你的耳朵拧掉。”我装疼,呲呲牙咧嘴还啊啊的叫。妈妈铺索了一下耳朵,又亲了我一口,说:“我娃最乖,把头剃完妈给你吃个糖。”我只能就范。
叔叔放下剃头担子,拉开摊子,给铜盆里舀了一葫芦瓢水,向铜盆下那个生火的铁皮炉子里加了柴,一会儿就听到火叭叭叭地响了,他用的是油松柴。他拉开抽屉,取出剃头刀和磨刀石,把刀刃两面上来回蹭了几下,用右手拇指试了试刀锋,再把手伸进水中试试水温,取来毛巾放在水中,用两个指头提出毛巾又放入水中,连蘸三下,提出来轻轻虐出大水,展开,毛巾热气腾腾,抖动两下先把我的头发焖湿,不烫了就焐在我的头上。稍后他拿起剃刀,扎个马腿,拉开了动刀子的架式。我看着妈妈说:“妈,我也要留和哥一样的文明头。”妈妈回答:“不行。你还没长大,不爱洗头,头上会生虱子。”妈妈对叔叔说:“剃。老样子。”妈妈没有一丝商量的余地。我的头还是被剃成了前面留一个手掌大的方块。
我七岁时,国家搞工商联营,号召支援家业,爸爸的家属—我们,连同户口迁回老家。
爸爸给我家买了一把剃头刀,每当我头发长长了,都是由妈妈给我剃。妈妈的手艺不专业,不会磨剃刀磨,剃刀越用越钝,后来剃头好象是活拨毛,剃完后头总是烧疼烧疼,为剃头我总是又哭又闹,小孩子家怎么能犟得过大人。每当听到拉得长长的喊音:剃头刀来—磨剪刀,我总会马上告诉妈妈。有一次妈妈给我剃头时,尽管她说了,刀子刚磨璨了,不疼。我的头还是来回拧得象个拨浪鼓,头被剃刀割了一条口子,妈妈从地上揑了一揑面面土止血,刚剃完头我硬是不洗头就跑了。因为妈妈忙,把给我洗头的事也忘在了脑后。那知我的耳根上夹着头发,几天后割耳了,双耳根都烂了,还化了浓。爸爸回家后看到了,买来一瓶云南白药,压着我挤了浓,上了药。还好,十天过去,我头上和耳朵上的伤全好了。
时间不长,爸爸又回家了,他带回了一把崭新的上海牌推子。
信是我邻居,来我家串门。他大我十岁,个头比我仅高一点点,他那个头是出格的扁而长,牙呲得象个山羊嘴,准硧地说是上门牙长出下门牙有半寸,牙齿影响着舌头的灵便,说话结结巴巴。他对我家的推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拿在手中一揑一放,反反复复。妈妈说:“信,你小心揑坏了,这推子要五块钱呢。”“这么贵!”他放下推子,又拿了起来,“没事,我舅是个剃头的,他也有推子,我玩过,他给别人推头时我常看,他还教我给一个人的推过头呢。”信哥拉住我,要给我推头。因为新鲜,我变得很乖。他推出来的头势果然好,我照着镜子偷偷地笑了好长时间。我的头终于变成文明头。
信那天连续给村里十多个大人小孩推了头,他后来成为我们村第一个顶呱呱的免费理发师。
十年一晃而过,电走进了农村,国营理发店很快就遍及了各个街镇。理发店里有电吹风,理发已涨价为两角钱,连吹风可要花五毛。有一次我去爸爸工作的集镇,进理发店臭美了一次,理发享受的是电推子,理发师打开开关,嗡嗡嗡的声音如音乐很好听,电推子挨着头皮,麻酥酥的感觉让我特别新奇,理发师问我吹不吹,我不知道吹什么,随口说了一个字,“吹”。师傅给我头上喷了发胶,把我的头发被吹成了波浪式,镜子里我看到了自已的发型,自感时髦极了,回家后几天都不敢洗头,怕破坏了我的头势。
我穿着黄军装,背着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黄背包走呀走,又走了好多年,才走到了农村的一个工作岗位。当年夏天,我来到城里出差,城市真新鲜,满大街的美女们不再把自已包裹得十分严实,发型个性,乳沟袒露,嫩腿性感,太惹眼了;公交车接踵而至,出行好方便,和陌生美女挨着坐或贴紧着站,心理上有一种特殊的滋味儿;宽大的影院椅如云梯,变幻的灯光引心入境,新电影很是撩拨人心,在电影院看电影让我体会到超级享受,把农村露天场看电影拥挤的场面比死了;四层高的百货大楼好耀眼,外面灯光璀璨,场内琳琅满目,我逛得好贪婪。我溜达着小心翼翼地走进了一家漂亮的发屋,理发师傅竟全是漂亮女子,在公开场合,女人用纤细的手为我洗头,偶尔触上我的脸,好舒服。师傅手艺好娴熟,一把剪刀,一把梳子,咔嚓咔嚓,咣当咣当,没动推子,理完发毕,我好诧异。理完发我问师傅:“多钱。”师傅用手扎了个八字,我给了一元,师傅说是八元,我的眼睛睁得鸡蛋大,那时我的工资每月仅三十七元,八元正好是我一个月的生活费。我抬头看到了一个镜框,是价目表,理发吹风8元,烫头15元。五天时间,我的月薪(一家人的生活来源)和出差补贴用完了,我琢磨着这个燃烧着纸币的天堂。
自然风总是由农村吹进城市,潮流风总是由城市刮到农村。农村集镇的男人专用的理发店改头换面成为发廊,女人喧宾夺主,成为主流。女青年走进了装修上档次的发屋,大辫子、羊角发经理发师的梳子剪刀进行改造调染,再把头装进有电烤的头盔里个把小时,传统的头就改头换面变得时尚,名星的头势随处可见。中老年女人进了发屋,后脑勺上盘着的圆转转的发型给梳直再烫弯,出店时变成了风靡数年的爆炸式的发型,黑丝线络络生产厂全部倒闭了。
一日,我走进一发屋,一小美女很热情,哥长哥短的和我搭仙着,语气很甜,耐听。在外边小孩儿都叫我爷爷,进理发屋我就被降辈儿了,变成了哥哥,小姐把辈分搞乱了,发廊也是。大师们都在忙着给女人染烫,她招呼我坐在了理发椅上,帮我围好理发罩。我用怀疑的语气问,“你能理发吗?”回答:“没问题。”是夏天,为凉快我要求理个寸头,可是这美女一推子推进了发丛,如同割草机开进草坪,她修了好长时间,无法填平我头顶的发坑,最后她为我理了个我有生第一次的光头。她撒娇而又认真地对我耳语:“大哥,小妹求你了,不敢声张,老板听到了肯定要炒我的鱿鱼,我就不能在这里学艺了。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不学咋能会理发呢?”我照着镜子看着自已这个十分滑稽的光头大哥难以名状地付了理发费。她说:“大哥,谢谢!慢走。欢迎再来。”我温怒地走出了店门,发现我把刚买的一本《读者》忘带了,折身取时,听到她正在对另一师傅说:“刚才我给那个老头子把平头理成了光头,傻老头还给了我钱。”我说:“小姑娘,说话不能太损了,因为你付出了比他人还要多的劳动我才给了你劳务费。”她回过头,脸红得如灯笼,“大哥,对不起对不起,你太能容人了,你做什么工作,我真想拜你为师。”我回答:“做人。”
五年后我融入了城市,又进一发屋,发屋里彩灯变幻,莫非又是新潮?师傅是一美女,那纤细而柔软的手待弄着我的头发,舒服,理发手艺一般,却十分利索。我当帅哥的年轮已过,已把时尚放在脑后。刮脸,她撩开后室的布帘子,引我进去。后室有一张床,我仰躺在床上,她一边用热毛巾为我焖须,一边给我按摩头部。刮完胡子,想不到的是她用自已的脸在我脸上蹭了一下,说:“光光的,不扎人。再做个全身按摩吧,让你放松一下。”我做过很多次的按摩,是舒服,同意了。她按摩着,很是骚情,一边用手不时的动动我的那个,让我的裤子翘了起来,又动员我释放一下。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很少有男人能经得住美色的引诱。钱是小事,可我忍住了,还真不是我情高,也不是我注重晚节,更不是我舍不得钱,也没想到会对不起老婆,我怕她有性病,我怕被公安抓住丢人,我怕这是个陷阱,尽管她说这里特安全,可我还是猛的起身,下床,凌乱着头发丢下一百元逃走了,我怕若有犹豫就会让防线崩溃。有惊无险。一不当心,很多的理发店变成了色情场所。
五年前,我理发时老婆就开始陪伴我,她很少坐着等,而是站着看,多数时间不开口,偶尔也提点儿建议。老婆算不上网购狂,可我家每天都能收到快递包。一日我帮她取回邮包,她打开后非得要我看,我发现是一套很齐全的理发工具。老婆说:“人家小女孩能在你头上学艺,我也学,以后给你理发我包了,免费。免得催你理发让我的嘴生茧。”真的我不喜欢理发,那水不是热就是凉,头发难免落到身上,扎得难受。第一次老婆开始理过发时,我对老婆说:“如果有人说我的发理得好,我就说是我老婆理的,还不一分钱不花。有人笑话我理的头难看,我就说这是在一个大理发店给理的,那师傅手艺还不如脚艺。其实你只要不给我理成阴阳头我都会满意。”老婆笑了。
老婆给我理发,我们总谈笑着,用风趣幽默逗乐子。三年前,她常数我的白发,数一根,就贴着头皮剪掉,硬是让他越数越多,应该是数不清了时,我和她一起乘公交车,竟有一小姑娘给我让了座。她下车后直接买来染发膏,在帮我理发时把我的头发搞得乌黑发亮,她前后左右地看,说:“精神多了。”我回答“有人给我让座你心理不平衡了对吧。”她帮我洗头时看到面盆里有不少落发,告诫我:“你可不能泄顶,那种光会刺眼的。”我回答:“你又不懂了吧,那叫聪明透顶。其实当个秃子能节约好多洗发精。”她说:“难怪你涵养(含痒)高,为了节省洗发膏有时三天四天不洗头。”三天后顺风快递就送来了首乌灵芝洗发膏,还管用,我的脱发有所收敛。我们家我们的二人世界时间多,我的理发间也就多是卫生间,这里有镜子方便俩人讨论头势,打扫卫生更容易,冷了打开浴霸,热了打开换气扇,我常一丝不挂,不担心头发落衣,理完当然是直接洗澡,老婆又附加了搓背的服务,这绝是超级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