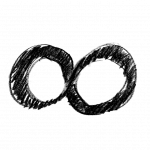将军山渡槽
叔本华在世的时候,他的哲学整整沉寂了三十多年。终于有一天,他像一位在枯燥的持久战中凯旋的英雄,声名大震,饮誉整个欧洲。很多大思想家、大文学家和大艺术家,都不约而同地聚集到这位哲人的旗帜下,其中就有存在主义的先驱尼采。

尼采的狂傲不羁举世公认。可是,他在提起遇见叔本华《意志与观念世界》的情景时,却这样写道:“一个不知名的精灵,悄然地对我说,赶快把这本书带回去!我一回到家,随即把我的宝贝翻开。我屈服在他那强力的、崇高的天才魔力之下了,恨不得一口气把全书读完。”
今晚,忽想写写故乡的将军山渡槽,也有一番和尼采相似的心情。耳边仿佛同样有个“不知名的精灵”在提醒,每一座上了年纪的老建筑,都是有思想的。尤其是一座历经五十年风雨积淀、几万双手花两三年工夫打造的老建筑。
将军山渡槽位于皖西大别山脚下,离我家不过几里之遥。在儿时的我看来,它是这个世界上最高、最长、最大的桥。它是架在天上的,是一眼望不到头的。
每次从张母桥经茶庵去广城畈的姑母家,都要从渡槽最南边的桥洞穿过。大桥高高地立在头顶,石头缝里砌着一丝令人敬畏的冷峻。桥下,一条清澈的小河淙淙向东,水中的鱼儿及河底的鹅卵石历历可见。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并不知道大桥和渡槽有什么区别。小学春游,一帮同学爬上将军山,惊讶地发现大桥顶上居然流淌着一条“天河”。那年头,乡下孩子的见识浅,从没见过更没登过高楼大厦。走在十层楼高的“天河”河岸上,同学们大都不敢往下看。有个胆大调皮的孩子,嬉戏时不慎踏过栏杆,一脚蹬空。要不是夏有炳老师眼急手快,一把将其抓住,后果不堪设想。春游之后,老师告诉我们,渡槽不是一般的桥,是架在两山之间引水灌溉的“天河”。
上初中,学《中国地理》课本,将军山渡槽的真实身份终于揭开:长840多米,高27米,拥有16个桥孔,是当时的“中国第一渡槽”。有了这座大渡槽,长江、淮河两大水系得以贯通,淠河、杭埠河两大灌区连成一体,龙河口水库的滔滔碧水,从此可以润泽六安东乡的几十万亩农田。
“将军山”这个地名挺特别的,但其由来无从知晓。
时间的河流有时很无情。多少鲜活的故事,都会被冲刷得无影无踪,只剩下一串串隐秘的符号。前几年去贺兰山,见山崖上的一幅幅神秘岩画,倍感震憾。明知道每一幅画都有来历,都是某个人或某一群人一笔笔刻就,可你用尽千方百计却探不清它的来路。符号是那么清晰,斯人却早已躲进时光的帷幔之后,表情复杂地注视着满腹狐疑的我们。
将军山渡槽也已经历了半世纪时光的冲刷。渡槽开建的那一年,美国的阿波罗号宇宙飞船首次登月,静寂的月球第一次印上人类的脚印。而在我的家乡,人们却依然缺衣少食,分水岭的农田也面临着“一方盼水水不来,一方恨水水不走”的尴尬。打通长江、淮河两大水系,是家乡父老的百年梦幻。正因如此,“南水北调”的号令刚一下达,三四万社员便紧跟着上头派来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赶奔将军山。
听老一辈说,1969年之后的两年里,在张母桥镇最西边的东岗一带,经常是红旗招展,人行如蚁,“千军万马会战将军山”的场面惊心动魄。那年头没有大型机械,没有工程车、起重机,没有混凝土搅拌机,靠的就是一双双粗糙的手,一副副压不垮的肩,一声声响彻云霄的劳动号子。据说,为给社员和工人搭建工棚,当地平整出的土地达200多亩。尽管如此,仍有很多建设者不得不借宿于生产队民房,有的甚至夜宿在社员家的鸡笼顶上。最忙的时候,这三四万人被分成多个小组,锹挖肩扛板车推,夜以继日三班作业。每天,他们的伙食,不过是八两米的稀饭。有梦想的感召,没有人喊苦累,没有人提报酬,没有人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面前退缩一步。
1971年5月23日,将军山渡槽竣工。那天,方圆数十里的群众都扶老携幼而来,共同见证这一“人定胜天”的奇迹。听说,竣工庆典的方式十分特别:放了一场电影,片名是《沙家浜》。
淠史杭工程委员会副书记魏胜德没能看上这场电影。作为渡槽建设的主要指挥者,他日夜坚守在工地一线。超负荷的工作,让他根本无瑕顾及严重的肝病。1970年11月,这位48岁的山东汉子在劳累和重病中永远闭上了眼睛,弥留之际,他一直在念叨“将军山…我要回工地去…”。
其实,像魏胜德一样为渡槽献身的建设者有近10名。我未能查到这些牺牲者的具体资料,但他们的英名理应永远镌刻在将军山上。
1974年,《人民画报》刊发了一幅将军山渡槽的彩色照片,那可能是这道人间天河最辉煌的一次亮相。与此同时,它也出现在几本地方编写的图书封面上。每次出场,渡槽的“天河”里都有一艘艘帆船御风而行。遗憾的是,我从没在渡槽里看到过船,更没看到过帆船。
热闹,总是一时的。随着千军万马的撤离,画报上的照片开始褪色,红旗飘飘的年代渐成远去的记忆。随后的几十年里,将军山渡槽就像一位寂寞的隐者,默默地活在人们的视线之外。只是,“天河”里的水日夜流淌着,从未止息,一淌就是四十七年。整整半个世纪,“将军山”究竟泽被多少农田,哺育了多少庄稼,恐是无法精确计算的。
沉默,有时候意味着深刻。前一阵回老家,专程去了一趟将军山。多年以来,我走过一座又一座长江大桥、黄河大桥,几乎每天都在都市的立交桥、高架桥下穿梭,但出乎意料的是,时隔多年重回这座渡槽,在我心中,它依然是最高、最大、最长的桥。我能深切地感觉到,有一股思想的力量从石头的缝隙间一点点渗出来,雄浑而伟大,令人无法抗拒。这力量的背后,是千万双粗糙而坚毅的手。
高大的桥头堡上,镌刻着一句简短有力又极为深邃的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轻轻读着这句话,禁不住想起尼采翻阅叔本华著作时发出的感慨:“我直觉到,我是很热心的注意倾听,我的嘴唇所吐出的每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