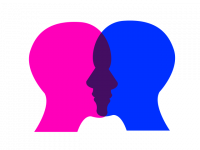夜啊夜
天,阴沉沉的。北风,时不时打个响鼻。街道比平时宽阔不少。三三两两的行人---大部分是年轻人,在路上溜达。绝大部分的店铺都关了门。高档酒店、洗浴中心、歌厅的大门,霓虹灯比星空还要壮观。几家西餐店,没有一个空座。这些年西风渐盛,热恋的人,富裕家庭的孩子,把吃西餐当作身份炫酷。

大红春联,在路灯下,呈现平安祥和的气氛,幸福团圆的年味。明亮柔和的灯光,远远望去,像一条扭动身躯的美女蛇。似乎,隐隐约约,又幻化成一个深不见底的洞穴。
凌余仁拖着沉重的步子,像个醉鬼,在大街上游荡。他身材矮小,瘦骨嶙峋,两鬓的头发已经花白。衣服单薄,这使他不得不过一会就疾走一阵。耳朵有被刀割的感觉,他捂着耳朵走,或者双手狠狠地揉耳朵。
走累了,停下来,倚着电线杆歇息。片刻,双脚木木的,全身直打颤,他赶紧走自己的路。
他的身影在街上移动,没有目的,没有固定的线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停下来。遇到路口,他完全凭感觉左转或右转,他知道:今天夜里,他没有什么事干,只有走路,走路,走路,直到天明。
他是被妻子赶出家门的---在这个除夕之夜,那个家,又不属于他了。
凌余仁记不清这是第几次被赶出家门了。他的工作不好。他的同事,娶的都是没有工作的农民,他出人意料地找了一个工作单位特好的妻子。娶妻子的时候,他拿不出钱,妻子却嫁给了他。他亏欠妻子,妻子也觉得委屈,常常半开玩笑半认知地对他说:“你是倒插门。”有了女儿,女儿也一脸鄙夷地说:“老爸是倒插门。”他的肩上压着一座大山,在家抬不起头!
他不听话的时候,妻子就往外撵他。开始他不想走,妻子就说非常狠毒,非常伤他的自尊的话,逼他离开家。那一次,他壮壮胆,毅然离开了家。在大街上混了一夜,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胆子迅速膨胀起来。再往后,妻子一撵他走,他就走。妻子不想让他走,只想让他说句软话,他不说,非要走!冬天,妻子让他把衣服脱了,他二话不说就脱,只留贴身衣服。一年四季,他经常在街道上过夜。
每次,凌余仁离家出走后,妻子就立即害怕起来。一整夜不睡觉。听到树叶哗哗响,就疑心是他推大门,赶紧起来开门。见不到他,满大街找,像个神经病人。
妻子经常发脾气,无论春夏秋冬。发脾气就往外撵他。尤其是过年,必发脾气。回老家,办年货,他没有年终奖,给孩子压岁钱,等等,都是发脾气的诱因。
凌余仁最怕过年,过年是家的灾难,也是他的灾难。他觉得,年是他的克星,他的黑道日是农历腊月二十五到正月十六。
北风,仍然带着哨音。街道上的行人更加稀少。高档宾馆的停车场,乌龟排队一样,停满高中低档轿车。洗浴中心,似乎弥漫着吴音软语。KTV包间,不知疲倦的歌声,诠释温柔富贵的天上人间。
凌余仁又拐进一条胡同。在大街上转的没有意思了,或者怕见熟人,他就走胡同。胡同道路狭窄,光线昏暗,行人不多,他的矮小、猥琐、狼狈,便悄然隐身,他的自信,自大,甚至狂妄,便慢慢苏醒。
偶尔,身上落下一片雪花。他鄙夷地笑了笑,继续走自己的路。
工作单位不好,又是普通员工,他在社会上和家里都没有地位。工资低,又不会干第二职业,捞点外快,他在社会上和家里很被人看不起。他是一个男人,男人应该是家的靠山,家的顶梁柱,妻子的取款机,孩子的通行证。他管不好家,别人认为他不是男人,他也觉得自己不是男人。更叫人好笑的是,他爱好文学,业余时间傻乎乎地写小说、写散文、写诗,周围的人说他是孔乙己,当面奚落他,叫他大作家。他听到“大作家”这三个字,就好像孔乙己听到有人问“你怎么连半个秀才也没有捞到一样”。
胡同很暗,他走路得十分小心。突然,一只狗狂叫几声。他吓得浑身是汗,头发直立。心想:狗也势利眼,欺负落难的人。
凌余仁特别害怕狗。和畜生斗,赢了,显不出英雄本色;败了,是别人传播的笑话。你不理他,万一被咬一口,倒霉的也是你。他只要见到狗,无论大小,就绕道走人。
幸好,狗在院子里。隔着高大的铁门,狗再威风,也伤不了他一根毫毛。他戏谑地笑了笑,迈开脚步往前走。
离胡同另一个进出口不远,有一家美容美发店。店里还亮着灯光。凌余仁路过店门口的时候,有一个穿黑色皮棉裙子的女人向他招手。
胡同里的美容美发店,不美容,也不理发刮脸店。这样的店,到处都有。就跟城市的小广告一样,也是城市的牛皮癣。店里,一般生活着几个姿色一般的中年女人。她们的空间是老年人、城市下层居民、农民工等。
凌余仁没有搭理那个女人,但是也没有鄙视她的念头。他甚至同情这类女人。“没有特长,长相一般,人到中年,她们不能像学生妹、外来妹、美少妇一样,栖身于宾馆、洗浴中心或者KTV包间里。她们的青春已经逝去,她们的价值即将耗尽。在别人眼里,她们没有地位,没有灵魂,没有人格。她们连装尊严的资格都没有,但是她们得活命,得养家,得给老人养老送终。她们是边缘化的人,是被侮辱与损害的人。除夕之夜,家家团圆,她们远离家乡,侮辱自己,陪着笑脸,让陌生人享受。她们的身上简直有耶稣的气味。”
他猛然觉得:他和她都是天涯沦落人,是同类项。他们同呼吸,共命运。他是她,她也是他。在这个美丽的世界,在拜金的浪潮中,在炫富的空间里,他们是失败者,是多余的。
风,似乎困了,无精打采地打哈欠。雪,来了精神,饱蘸她的激情和速度,落在楼顶,落在街道,落在田野,落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在她的眼里,世间万物是她的婴孩。她必须尽快做一条厚厚的柔软的棉被,隔离冬的冷酷和残忍。
在除夕之夜,在这个白色的大地上,迷恋街道的,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和四处是家的傻子。其他的人影,都是匆匆的过客。
凌余仁的头上、身上落满了雪花。洁白的柔软的雪花,打在脸上,像掌掴一样疼;飘进眼里,有酸涩的感觉。他的脖子有些僵硬,十指发麻,像有一些蚂蚁在上面爬动一样。双腿木木的,没有痛感。
他想止步歇一会,但是理智告诉他:世界是一块坚冰,万物是一块坚冰,就连路灯发出的光线,也是冰做的。如果你还想活着,就不要停下脚步。他想起了夏天的好处来。然而在夏天,闷热和蚊子折磨着他,使他多次感叹:“天啊!要是在冬天,那该有多好啊!”
在繁荣路和尚德路交叉口,凌余仁脚下一滑,重重地摔了一跤。他一边骂娘,一边小心翼翼地爬起来,一瘸一拐地登上两个台阶,走进某家店铺的走廊里。借着雪光,他看见走廊里躺着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
那个人的头发长而乱,上面沾满碎叶、稻草。脸又黑又脏,像抹了一层煤灰一样。穿着一件没有袖的露出鸡毛的黑色羽绒服。肥大的棉裤,前后开档,露着大半个屁股。脚上的老北京布鞋,露出脚趾。头枕一个鼓鼓囊囊的编织袋,蜷着身子,侧卧着。
凌余仁认出了那个人:他是个傻子,外号交警。一年四季,站在路口指挥交通,风雨无阻。
凌余仁心里一酸,眼泪和雪花混在一起,模糊了双眼。他从衣兜里掏出半瓶酒和两个烧饼,递给傻子。傻子笑了笑,拧开酒瓶盖子,咕咚咕咚,一饮而尽。
“有人说”,凌余仁心想,“傻子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命倒是硬朗;傻子不知荣辱,无忧无虑,倒也是逍遥神仙。天上悠闲自在的神仙不多,人们想羽化成仙;人间命运多舛的傻子太多,人们避之不及。唉!凌余仁,你就是个傻子!和躺着的那个一样。”
没有风声。雪,任性地下着。这一元硬币大小的,繁密的雪啊!洁白似玉,美丽如花。也许,她们历经磨难;也许,她们刚刚出生,也许,她们正在做一个甜美的梦。然而,为了一个信念,为了一种担当,为了一份坦然,她们毅然决然地落到人间。她们知道,落下来,就是赴死,流星一样,凄美地,死去。她们是可敬的天使,是人间的殉道士,盗火者!
凌余仁的眼睛又酸又痛。眼中的路灯,奇怪地移动,光线忽明忽暗。时而,几盏灯,模糊成一团,像白色的或黄色的云雾。双腿,没有知觉,就像别人的汽车轮子。头发和脖子湿漉漉的,像鼻孔、嘴巴一样,冒着白雾。
在人民医院大门口,仿佛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凌余仁赶紧躲进医院。
人民医院住院部有暖气,有几次,他倚在暖气片上,享受别人的恩赐。
凌余仁麻利地找到那个救星,闭上眼休息。
远处传来急促的鞭炮声。接着,整个城市沸腾起来。噼噼啪啪的响声,像成千上万个黄河汉子,用粗犷的嗓音,奔流的血液,豪迈的激情,一起吼春,一起释放,一起爆发!声音传染声音,声音助威声音,声音淹没声音,声音催生声音。噼噼啪啪!噼噼啪啪!!噼噼啪啪!像狂风横扫大地,如海啸袭击海岸,似千军万马决战沙场。
新的一年,新的一年到来啦!不管你富贵贫穷,不管你尊贵卑贱,不管你是春风得意还是颠簸流离,新的一年,都会带着微笑,向你走来。
在新的一年里,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拥有同一个太阳的不同的人,还会扮演不同的角色,讲述不同的故事。
凌余仁摇摇头,又进入梦乡。
黎明,人民医院传出凄厉的哭声。凌余仁正在做自己成为受人尊敬的人的美梦,猛然惊醒。他笑了笑,狼狈溜出医院。
地上的积雪大约半尺厚,亮如银镜。街道两边的梧桐树,冰雕玉琢一般,煞是好看。凌余仁的身影,长长地映在雪上,像断线的风筝。明亮柔和的路灯,晃动,模糊;模糊,晃动。远远望去,恍如扭动着腰肢的含笑的美女蛇和吞吐万物的灵异的洞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