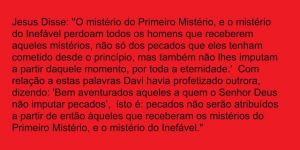倾城之雨
有一些事物是人无法挽回的,我们只能看着它逝去。

——伊森?马尔森《暴雨》
入伏的七月天随时都会像猛然被掀开的笼屉,那一会还焦躁得喘不过气来,这一会又暴雨倾盆。短短的晚饭时间,我就被暴雨堵截在食堂里。平时我是不会放过将烦恼忧愁冲刷殆尽的这份快意的,奈何身上那寸长的伤口,我也只能低头。打开手机的播放器,此时最适合单曲循环的歌应该就是罗大佑的那首《倾城之雨》了。坐在饭桌旁,熟悉的旋律又一次像斗大的雨滴拍打着我的心扉,我的思绪犹如这突降的暴雨倾泻而出。
2004年,第一次拿到《美丽岛》的CD,最喜欢的就是这首歌。那时没有网络,电视和报纸也只会说罗大佑扩别十年又发行了一张专辑而已。老罗那撕心裂肺的哭腔中一定有故事,到底是什么故事?我不知道,也不懂。
没用多久,我就懂了那首歌。2005年的牡丹江沙兰镇,一场暴雨夺走了100多名孩子的生命。电视上慢慢滚动着遇难孩子的名字,背景是曾被用作《风云》插曲的童声《虫儿飞》,我却猛然想起那首《倾城之雨》。一刹那,对将生命扼杀在青春年华的司命神的悲情控诉,对死不瞑目的那群孩子的深情慰藉,对那些武断专行选错校址的大人的愤然声讨……我竟然觉得,那是罗大佑为这次悲剧中丧失的孩子提前写好的葬曲。
后来,我就把这首歌忘了,直到又一场暴雨引发的悲剧传入我耳中,我才又猛然想起它。这次,受到暴雨袭击的是首都北京,61年有气象观测以来最大的暴雨。因为是首都北京,和远在黑龙江的沙兰镇比有最好的排水系统;因为是首都北京,不会像山沟里的沙兰镇把学校建在山坳;因为是首都北京,灾害到来时不会像沙兰镇的村民那样知道自己孩子在泥水中挣扎束手无策。即便如此,依然有37名市民遇难。
遇难的数字终于超过35了因为这是纯粹的天灾没有人需要承担责任,演员再也不用因为片场山高路远难免迟到而向导演道。网上依然爆发着暴雨般的讨论,一年前的动车时是这样,四年前的地震也是这样。四年前网上铺天盖地都是日本的地震怎么怎么多,人死得怎么怎么少;
一年前网上铺天盖地都是日本的新干线怎么怎么多,事故怎么怎么少;现在网上铺天盖地都是日本东京雨量怎么怎么高,排水系统怎么怎么好。这无可厚非,我们为死者哀悼的同时必须反思更多的东西。就在7年前,我高中时代的同学都了解我,那时的我盛气凌人,我在为那些遇难孩童流泪的同时也破口大骂政府里坐吃山空无所作为的领导,后来直至现在,我就变得只会单曲循环着《倾城之雨》为逝者祷告了。
想不起这首《倾城之雨》,我也不会去搜索它,可能以后也不会知道这首歌背后的故事。一个正值青春年华的女孩被绑匪绑架,绑匪剁掉她一个手指并百般蹂躏以向她的母亲,台湾着名演员白冰冰索要赎金,在得知白冰冰报警后绑匪愤然撕票。《倾城之雨》正是罗大佑为这个叫白晓燕的女孩所作,在感叹她身世浮沉的同时希望她能安息。以往的罗大佑,不让他骂人他是万万做不到的,这首歌中却看不到多少对凶手乃至社会的谴责,也许再多的谴责在生命凋谢的沉重感面前都太苍白的缘故吧。
政治总是给人以太多的话题,生命却不是。我们的社会会七十二变让我们眼花缭乱,生命却永远只有两种形态让我们或悲或喜。我是在进入社会才开始沉默寡言的,因为我发现只处在相对安全的地方才敢骂娘实在太无耻。白天作为社会人的我成了萨特所定义的同谋,晚上坐在14寸大的井口前天不怕地不怕喷吐着口水。
我可以做更多,但我不敢。我知道哪怕让我失去一点我拥有的和想要的,我那满腔的正义感都会打退堂鼓。每次当网上疯狂转发一些抗议时,我都不再参与,我只要默默替死者祷告就够了,只有这个我能确定自己是真挚的。四年前是,一年前是,现在仍是。
一场倾盆的暴雨中,史考特的双胞胎哥哥约翰与他在一座建筑工地玩耍时,被卡在一个打开的排水管中,史考特终没能说服他们那醉酒的父亲去救约翰,最终约翰在暴雨中被淹死。
史考特后来被人领养,他以他哥哥的名字约翰·舒伯特实施了多个计划,每个暴雨倾盆的日子他都会绑架一个孩子然后通知孩子的父亲,试图找到一个父亲,做到他自己的父亲办不到的事。两年来,已经有8个孩子被他撕票……这是PS3独占大作《暴雨》的背景故事,也是开篇那句话的来历。那位叫伊森?马尔森的父亲就是第九位,不同的是,他做到了。
我在想,我们的社会是不是也遭遇了一个这样的折纸杀手,在每一个暴雨倾盆的日子为我们埋设如此的灾难。我们多数人都会如马尔斯的妻子那般埋怨马尔斯丢掉儿子的同时撂下一句“我欠他太多”和几滴眼泪,却没有一个马尔斯站出来用巍峨的父爱去迎受那五项考验,你不敢,我也不敢。姑且流下几滴泪吧,肯定有兴致和态度埋怨的人,至少他们是有正义感的,感谢无私向遇难者施救的人,他们甚至愿意用自己的生命让悲剧最小化。
回到这首倾城之雨,屋外的雨伴随着电闪雷鸣,这次恐惧的变成了我们。至少这首歌的宽慰让此时的不算太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