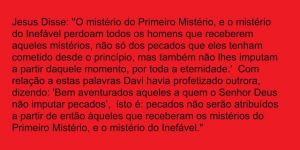蜻蜓舞麦场蝉噪好野眠
怀旧是每个人都不能逃离的情绪,不是因过往都美好,也不是因如今太寂寥,皆因感情的行囊必须装下这些,才可旅行,才可安日,才可安顿一颗心,就像一抹清凉油涂在眉梢,眼睛会辣辣的;就像乡土的晚炊弥散在你的鼻息,撩手赶走却入心……

四十多年前,我家的老屋前面太奢侈了,门前便是路,路与一面场地相连,大小应该不小于一个篮球场,只是不规则,它的东南面一角是半圆,半圈绕了便路,把场地高高擎起,似乎是把个孩儿扛在大人的肩上,宠着,颠着……
秋收时节,这片场地的肩膀就重了,周围邻居家的草垛沿着场地周围堆满了,堵得不见一丝儿风,只有草垛之间为了有个界限而留出了小孩子勉强可以钻过去的当儿。中间是谁也不敢贪为己有的,生产队上的积肥场天经地义在那里,周围并未划定一个红线,但大家都恪守那份公私的分界。
儿时玩捉迷藏就在这里,但名字不好听,大家都说是“粪场”,很不文雅,但一直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篡改。这个名字只有到了入夏麦收季节才焕然一新,成了名副其实的“麦场”,中间的土肥都已经趁着麦收前的空闲搬走,堆在了地头,以为夏种之用。
自留地的麦子的敲打晾晒就在这里,占用场地不看谁家是否有实力,谁家的麦先收割了谁家就先在那晾晒,一旦又有邻居割麦上场,马上扫到一边,腾出场地。常常念想那是的纯朴无争,无需谦让,随顺了自然。
记起两句诗来——鸟穿浮云云不惊,沙沉流水水尚清。麦收时节是忙碌喧嚣的,但农人的境界却是不惊之云,清澈之水,内心的执着很火热,只是不能贪得,都在那片场地里,尽管转转身就碰到了屁股,可他们的世界只有那球场一般大,没有人嫌小。
燥热,是夏日麦场的主题。唯有融入这个主题的是蜻蜓,不知为何那么准时,我疑心是闻着了麦香而来,又疑心这些最会翩舞的使者就藏在麦场的某个角落,那为什么我们捉迷藏就没有无意撞见?
蜻蜓的诗,在我曾经的抄录本子里,占据了很大的篇幅,或许因我对其独钟。范成大的“日长篱落无人过,唯有蜻蜓蛱蝶飞”我觉得不够真实了,明明蜻蜓绕着我们蹁跹,怎么说蜻蜓惧人呢!写蜻蜓,刘禹锡是高手,情趣难忘:“行到中庭数花朵,蜻蜓飞上玉搔头。”我未见蜻蜓恋花,却见蜻蜓落在捡麦穗的妈妈头上的玉簪上。
有时候,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那些绿水青山,那些改变是眼见的,还有我们难得一见的乡情,乡情不仅仅是心底所思,还有那些感性的画面,以及画面里时而嘤嘤或时而喃喃的发声,尤其是如蜻蜓轻落玉簪的绝对慢镜头,往往这些栩栩如生的画面,可以定格了一个时代的最美,留住了一个人对过往的痴恋。
不敢奢望了,所以我常常欣幸那些作家可以把那些年份的东西描摹出来,即使不对我的胃口,与我所见所感有异,只要可以勾起我的一点记忆,发酵了我的乡情,便以为他就是高手。
乡情的感性总是可以牵动我们的心,在眼前盘桓而不去。曾记得,天边若因热气压缩了一片云,是否是雨滴的前奏不得知,但那蜻蜓总是于此时蓦然从天而降,只做半人高,款款的,那时没有直升机的概念,她可以静止于半空,持久不遁,因我们的性情不坏?因麦香堵塞了她的灵感?恶作剧从来都是孩子的意趣,赶紧找来一把大扫帚,但你必须静静地在空中悬着,待那蜻蜓入了被捕的防线,扫帚凌空扑下,一下子按住,但不敢也舍不得用力,但愿扫帚之下的蜻蜓还可以动弹,若是一动不动,心中马上多了自责错咎的不忍。可以放进用草杆自编的小笼子,悬在门楣上,吃饭举首可见,好下饭,心中想,下饭与此真的无关,可能是心情使然吧。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总是能给人一种力量,那种力量是难以形容的,却不难感受。但为何那时却冲动地想着法儿要逃离这个麦场的温馨与快意呢?要与那些蜻蜓告别呢?为何要激情地冲出那个老家去陌生的地方读书谋生呢?最本质的是,情趣这个东西很别扭,不能以为谋生的手段,只能是谋生不愁以后的激素,发酵了闲静的日子,多了一份享受人生的曼妙,若没有这样的感性,我以为人生都很残缺。若谁把情趣作为谋生的手段,那他一定碰壁,至少是一个阶段的脑子进水,若有了谋生的现实,发展了那情趣说不定可以在添加生活情趣的同时,多了一份谋生的手艺。
那时,在老家,要说很奢侈的,那就是“野眠”,这个词是听一个高中生说的,他早就死去了,只留下这个诗意十分的词儿。老屋的旁边有一棵梧桐树,还有一棵是老榆树,枝叶繁茂,铺天盖地,但很知趣,从来不遮掩麦场的阳光,在蜻蜓来了的时候,也约了蝉儿,有时候心燥得很,越是天热的时候越是音调高八度。现在想,若没有了蝉儿,还是夏日么?麦收完了的第二日我总是要快打一挂麦帘子,麦秸捋顺,中间用细细的麻绳拴住,夜晚在院子里铺开,经露而润,除却那些“麦毒”(若不经露而贴身往往身上起泡)。在老屋身边,没有时光的概念,只有与麦场相始终。名义上是为了看住那些鸡,不要来啄麦,但草帘子铺在树下的荫庇处,头下垫一块砖头,一把蒲扇摇了没几下就累了,弃在一边,沉沉地睡去,蝉儿总是烦人,其初几日,你会把蝉儿视为天敌,为何要来烦扰人的午休!
老家的蝉儿分出三类,一是“马勒猴”,个头硕大,叫起来惊天动地,声音却慢条斯理,正好是睡觉的节奏;另一种是“嘎啦”,满身泛绿,就像那在沉香木上刻字填色的那种“明矾绿”,鸣声嘶哑,似有难言之隐,有点像嘶哑的萨克斯?或者就是喘气不匀而奏起的管笙?最末要轮到最让人看不起的“婕拉”,样子扁小,声音就像是那些初上舞台哼流行的那些小孩子乐手,只是那些同伴喝彩,没有人可以竖起大拇指。
麦秸草帘子就铺放在那树下,蝉儿尽管噪,不敢说是交响曲,至多是老屋前不会萧条的热闹,一条白色的毛巾搭在肚皮上,蝉儿在耳畔嘶鸣,这“野眠”不是很沉的那种,脑子里是阳光的炫目光环,仿佛一睁开眼就被灼伤了,只有声音伴眠,说来也怪,声音是睡眠的敌人,此时此境可以成为催眠,实在让人弄不懂其中生物钟为何可以这样适应。
经历了失眠,慢慢沉想,原来心事总是失眠的障碍,与声音无关。有人说,只要大累一场,你就是用麦秸秆撑起眼皮都不能让人不睡,但还是不能解释一些失眠的现象,其实,若心中只是想着一件事,且毫无追索其果的愿望,就贪睡;而失眠多半是自寻的烦恼使然,若你大脑足够装得下,那烦恼来袭就袭吧,驾驭全在一颗心,不惊不惧不思,这是梵音境界,但多少人可以达到这样的超脱臻境呢!
很多时候,烦恼了半天,却什么事也没发生。你不能出来,就钻牛角尖,自然“烦恼绵绵无绝期”。这些问题的解决完全来自内心的静如水,其实,这是不负责任的答案,若你只是告诉自己,野眠之后再来处理也不误事,总比耿耿于怀的好,于是那些蝉儿就成了催眠的曲子,不管合不合乎音律,都不在话下。眠去,蝉无声;眠去,太阳不扰;眠去,鸡啄麦也不顾,麦场上剩下的总比啄去的多……
一个千锤百炼的词叫“返璞归真”,何其难也!人生的意趣很多都是不能归于本真的,“返璞”也只能是文字里的惦念与玩味,唯一的用途就是勾起人对过往的痴迷,单调的现在不能没有一点佐料,于是添加了“开轩面场圃”的画面内容——蜻蜓舞麦场;于是不舍那野趣而在蝉噪里或浅或沉的半眠。旧时一隅老屋旁的麦场,原始的美,穿透了我半世的人生墙垣,又破了耳鼓,直入了心底的情趣最软处,不能放过蜻蜓舞,不能放过蝉儿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