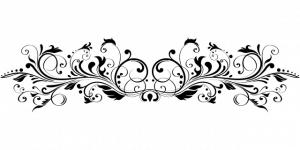记忆中的“美味”
啥叫“美味”?网上说“美味是指人们口腔对鲜美食品的感觉味道很好,很可口,让人能产生食用的欲望”。这是针对人身体上的器官而言的。其实,“美味”是活的,它在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条件下,有着不同的含义。假如你出生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饿得你奄奄一息,给你个米糠做的窝窝头,你是不是认为它是“美味”?再假如你腆着个啤酒肚,在高级大酒店吃惯了山珍海味,给你个极香的鸡大腿,你是不是认为它是“美味”?

常听妻子抱怨现在做饭都不知道吃啥?!也常看电视上热播的“舌尖上的中国”。但那些让美食家们啧啧称道的人间佳肴,却在我吃的记忆里没有留下一丝难以忘怀的痕迹。
留在我记忆里的,只有母亲那一年用清亮的菜籽油,炸出来得那一盘喷喷香的水虿和妻子那一盘芹菜炒鸡蛋。这记忆始终盘绕在我的脑海,想忘都忘不了。每一次回想起来大都是馋涎的要流口水一般。
(一)
我家的斜对面是一片地势很低的庄稼地,庄稼地的东面便是一个很大的雨水坑。每一次下大雨,村子里大街小巷的污泥浊水,夹杂着烂布碎柴和满街的鸡屎猪粪,都会汩汩的流动到这个水坑里。久而久之,这一片污浊的雨水坑就成了村子里一个永不干涸的“湖泊”。
水坑的边缘都是黏黏的胶泥土质。在水坑边缘上生长着密密麻麻的“老鸹”干粮草。据村里老年人说,“老鸹”干粮草,是专门长给“老鸹”吃得,但我和小伙伴们却不去理会这些,每天都争抢着去水坑边上拔着吃。
这草很奇特,先是长出来一条条薄而细长的叶片,到春暖花开的时候便从叶片的中间吐出类似高粱穗模样的果实来。这果实嚼在嘴里,醇香悠悠,满口生香。每次下学以后,小伙伴都像一个个爬在地上的大蚂蚱一般,撅着小屁屁用小手在草丛里寻觅,看准了便用两个手指甲掐住,轻轻的用力将果实拔出来,假若你性急用力大了,那小小的果实是断断拔不出来了,最后只能在你的指甲缝里看到一星点碎绿。
记得那年正值青黄不接(麦子吃完,秋庄稼还没有打下来),家里已经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娘看着我们姊妹三个饥黄面瘦,心疼不已。
那天娘拿着家里筛面用的筛子,挽腿下到已经有些许凉意的雨水坑里,捞上来好多丑陋的水虿。这水虿有大有小,大眼珠子在脑门上一边一个,圆圆的就像婵的眼睛那样突兀的闪着亮光;黑色的斑点像雨水坑底的污泥一样布满全身,再加上那前倾的扁扁额头和支扎着的六条细腿儿,你要仔细看过了,多半会认为:这水虿生的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娘出生在邻县的大河边上,据说水性极佳,在我村却只有这个泛着臭味的雨水坑,使我一生都没有见识过娘的泳姿。但倒是常听娘谈起她小时候,在清凌凌的河水里摸鱼捉虾的趣事。能突然想到这雨水坑里的丑陋生物,也许这跟娘出生在河边、玩耍在河水里有关。
娘把捞上来的水虿放在脸盆里,用盐水洗了又洗,然后放进加热了的油锅里。
等娘从油锅里把水虿捞出来,这丑陋的小东西越发的难看了。
只见圆圆的眼睛已经凹了进去,没了一丁点光泽,那支扎着的六条腿也齐齐的伸展着向身体的后方蹬去,只有油汪汪的菜籽油在它们身上泛起了浓浓的香气。
娘示意可以吃了,我们姊妹三个却怯怯的望着那些更加丑陋的水虿不敢用手去拿。娘便拿起一个放在嘴里咀嚼。做为老大的我试探着拿一个水虿放在嘴里,先是轻咬一口,那鲜鲜的香味便浸入我的喉咙,于是,我猛嚼几下把水虿整个吞进了肚里,又伸手去碗里抓;这时候,那四只小手便不在迟疑,纷纷的往碗里抢来,很快将水虿吃了个一干二净。
娘这时候站在我们旁边,定定的看着我们姊妹三个狼吞虎咽,直到我们吃得满嘴流油一个不剩,娘才端过来一大婉温水来,让我们一个个喝过,娘的脸上也透出了满意的笑容。
啥是美味?那时候这丑陋的水虿便是“美味”!
(二)
八十年代末期,有了女儿,我在城里工作,妻子带着孩子在农村种地,家里日子过的很是拮据。妻子很能吃苦但也是很要强的一个人。
记得那时候,父母给我们兄弟分家,我分了一个独院加五间房,这五间房有两间没有盖房顶,盖了房顶的那三间下雨时也总是漏雨。妻子一心要把这房子拆了重盖。家里的日子过得更加紧把起来。
妻子没跟我结婚的时候,也是在城里工作的,只是有了孩子才回到农村。其实地里的活计她是一点都不懂的。但她很知道用心,看人家怎么种她就怎么种,而且有一股玩命的劲头,只要走到庄稼地里,假若庄稼地里的农活半天干不完,她就会在地里摘些自家种的西红柿、茄子之类的蔬菜垫补一下,然后一整天不回家,直到把庄稼地里的农活干完为止。
待到收获季节,妻子的勤劳使我家的地里收入,居然比别人收的还要多。特别是妻子种的花生,不但收成好卖钱多,那种出来的一堆堆匀称饱满的花生,也让好多种花生的行家里手都赞叹不已。
她还在家里养鸡,晚上用一个灯泡在鸡窝里照明,据说这样可以让母鸡下更多的蛋。但不管这老母鸡下再多的蛋,她都是舍不得让我和孩子吃一个,大都是换成钱。记得妻子听说有公鸡的老母鸡下的蛋更值钱,她便去集市上买只大公鸡抱回家来。
那时候我也是很节俭的。每次在单位打饭,我都是等到别人都打完了才去,那样,好吃也很贵的菜卖完了,我只能买最便宜的菜,这样既省了钱也保全了自己的面子。记得那次单位组织去旅游,包管每个人的交通费和景点门票,但是不管吃饭,我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没有去,因为我兜里仅剩的二十元钱,给了妻子十元,剩下的这十元是留着我在单位吃饭用的。
那一天大概是我生日,妻子格外开恩,中午去地里将她自己种的一垄芹菜拔回家洗净了,先是把鸡蛋炒熟,那鸡蛋像涂了黄颜色一样焦黄焦黄,然后把芹菜用开水焯一下,那芹菜更是嫩嫩的翠绿,这两者搭配起来,黄的焦黄,绿的翠绿,好看又好吃,我足足的就着馒头吃了半小锅。
啥叫“美味”?那时候妻子炒得这一盘芹菜炒鸡蛋便是“美味”!
记忆中的“美味”还有很多很多。
前几天在超市买了几个粗糙的窝窝头,做饭时腾热了,妻子和女儿便跟我来抢,也许这窝窝头如今在不少人的眼里已经成为“美味”了。
翻开尘封了很久的往事,记忆里的“美味”历历在目,比如红薯面窝窝轧出来的饸烙面,榆树叶子和玉米面篜成的窝窝头,玉米面烙的“翻身饼”等等。这些记忆中的“美味”有的在时代的变迁中消失了,有的成了怀旧饭桌上的香饽饽,但不管时代如何变迁,这“美味”都镌刻着时代的烙印,这烙印因人而异,在透着酸甜苦辣的人生之路上,书写着各不相同的滋味。